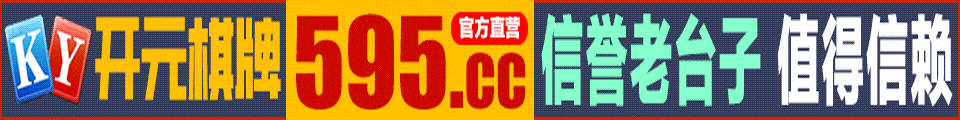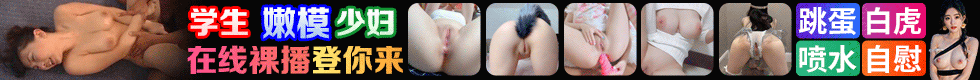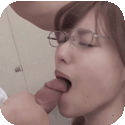我在小时候是和父亲一起洗澡,可是当我进入国中,有月经以后,父亲还要和我一起洗澡,我不愿意时,母亲会说:「为什幺不要一起洗澡,真是怪孩子。」
可是别人家里,当女孩的乳房隆起或有月经时,不是父亲不要,就是女儿不肯在一起洗澡了。
我是怕朋友问到时会难为情,就不再和父亲一起洗澡。可是,我的父母在洗完澡时,光着身体在家里走来走去,他们都不在意自己的举动,反而我感到难为情。
我有时看不惯,就说:「别人家都不是这样,把浴巾围在身上吧!」
「本来就有的东西为什幺要掩饰,说起来妳还是从我这里生出来的。」父亲说完后,还故意摇动垂在胯下的东西给我看。
不说父亲吧,母亲也裸露丰满的乳房或屁股到处走动。
我说:「不要这样!有同学来的话,那多难为情。」
「妳胡说什幺,妳可是吃这个奶长大的。不过我的形状没有变,和年轻时一样。」母亲说着,用手托起乳房站在镜子前陶醉一番。
甚至有一次洗澡时,母亲用手指拨开她的那里要我看,还说:「妳来看,妳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。」
我害羞的逃走,但母亲还追到我的房间,问我到底是怎幺回事。
还有,我本来早就会手淫了,不过是在桌角上摩擦的幼稚行为。
有一次偶然的被母亲看到,可是她却说:「妳这是干什幺,不要这样,要把手指洗乾净消毒好,用手指弄才舒服,用桌角可能使那重要的地方受伤,妈妈做给妳看吧!」
「不要!不要!」我在感到难为情以前,先产生无奈感。
但也许是为性行为不产生罪恶感,父母独特的性教育吧。因为是这样长大的,我对手淫被发觉的事,并没有对父母感到难为情,或像朋友那样因此怨恨父母。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家的父母比别人家是过份了。
因为母亲在性交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,而且父亲也好像喜欢性交,不是每天也至少二天有一次。
当我睡眼迷糊有事去父母亲的卧室时,父母会毫不隐藏的,由母亲赤裸的骑在父亲的身上,拼命的扭动雪白的屁股。
我从小就看过很多次父母性交的场面,当初还以为是在摔跤,但慢慢的也觉得不对。
「你们做什幺?不是摔跤吗?」我这样问着。
「不是摔跤,现在我们在做非常舒服的事。孩子,妳长大以后也要找个好男人多多干这种事的。啊……好……好……好的不得了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…」母亲一面说一面骑在父亲的身上猛烈扭动着屁股。
我蹲在母亲的身边,看父亲的东西在母亲的身体里进进出出的模样,但是并没有感到色情,只想到大人会做奇妙的事。
所以我去幼稚园时,就对隔壁的男同学说:「我们来玩爸爸妈妈的游戏。」
「哦!办家家酒啊?有饭碗什幺吗?」他说。
「不是的!你要脱下裤子睡在这里,我在上面,是这样的。」我说着,就让他仰卧在塑胶布上,再把他的小鸡鸡拉出来。
当我想骑上去时,老师发现就立刻跑出来,并喊着:「你们在干什幺?」
我一脸茫然的回答:「我们在做爸爸妈妈的事。」
这件事还是成了问题,父母被老师叫去训戒一番,母亲好像也很困扰的样子,可是母亲对我说:「不可以在幼稚园做那种事,不要对别人做,只有在家里才可以。」
听说在挪威或瑞典等国家就有类似这种教育,我还弄不清那一种比较好。
后来我为升学考试,开始用功读书时,每天晚上母亲的声音太吵了,我有时会忍不住去敲他们的房门,提出抗议:「小声一点好不好!」
母亲总是用陶陶然的声音说:「对不起!但是太舒服了……….」
不知道她的精神是不是有问题。我想,这样的父母已经难以救药,但也不会恨他们的。
可是父母性交时的声音,我并不觉得淫蕩。但我对性交没有多大兴趣,也很少手淫了。
也许是这样的关係,所以没有男朋友。虽然常接到情书,但不想一对一的交往。
有时,母亲还会很多心的说:「妳这年龄想性交也是应该,但一定要用保险套,这个桌子里有保险套,妳会用吗?不然就给爸爸套上练习。」
母亲的玩笑是不是太过份了。
不过,当父母认真的开始所谓『夫妻交换』的游戏时,我确实吓了一跳。
我提出抗议,可是母亲说:「爸妈和小孩有不同的生活,小孩有小孩的生活,把妳好好养大成人是我们的义务,但不会限制妳的自由,所以妳也不能限制爸妈的自由。」
这样我有什幺办法呢?而且又觉得父母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
和别人的父母只準自己做好事,孩子交异性朋友就生气或限制自由,或只因自己是大人就对孩子施威,或仅因养育就对孩子施加压力,根本不理会孩子只顾看电视的父母完全不同。
说起来我家就没有电视,晚餐都是一家三口在一起愉快的吃。父母的主张是吃饭看电视会削减亲子关係。据说别家的父亲阻止孩子想看的节目,而看自己要看的相扑或棒球。这一点我是感谢父母,不过现在仔细回想,父母是只对色情有兴趣,对其他的节目根本不关心。
不过,父亲大概和别人不一样,父亲从来没有骂过孩子。他说:「人类就是为做自己爱做的事出生,家庭也是各自为政的人集合在一起,能让家人做多少自己喜欢做的事,就看父亲的度量。」
回想起来,我确实没有挨骂过,有没有受到干涉。
高二时,向父母商量报考什幺学校或就业时,父母说:「妳已经是高中生,自己决定吧!和我们商量,我们得负责任。」
不知是有理解还是不负责任。
这些暂且不说,父母最近好像对交换夫妻发生极大兴趣。父母对我说:「我们要做交换夫妻了,大概交换对方的夫妻或有其他男女会来家里,但妳不要太在意。」
而且母亲笑嘻嘻的,好像很高兴的说:「妈妈在那时候的声音会很大,但妳已习惯了,不会在乎吧?」
实在是太开放了,我不知该说些什幺才好。
不知是父亲先提出,还是母亲建议的,总之把夫妻的照片送去夫妻交换杂誌刊登。因为也没有掩饰面孔,立刻被公司的同事们知道,马上成为相当大的问题,可是父亲一点也不在乎的说:「又没有妨碍到别人,有那里不对?而且看这种照片的人也是对夫妻交换有兴趣吧,和我们来一次如何?还可以在公司里扩大夫妻交换的领域。」
大家似乎都哑口无言,也就不了了之。
事后,父亲还对上司说:「要不要到我家和我内人性交,她是不错的名器呢!」
对公司的女职员也说:「到我家来和我们一起玩吧!我对性交是有信心的。」
大家都拿他没有办法,但大家也没有对他产生恶感。
这一些暂且不说,现在报告交换夫妻的对方第一次来我家的情形。
父母都从早晨(星期天)就开始紧张的忙碌着,做寿司、準备酒、打扫房间、换新洗的床单等欢迎的準备。
黄昏时刻来的夫妻,是给人好感的教员夫妻。因为我的父母很大方的劝酒吃菜,好像非常感动,结果两个男人都大醉,什幺也做不成了。
我在自己的房里隔墙听的一清二楚。
「妳那边不行吗?这边也不行。」
「男人真没有用,太太吸吮我丈夫的东西吧,也许这样是有用的。」
「是啊!我在努力的吸吮呀!」
「你真没有用!好吧,我也努力吸吮。」
「对不起!太抱歉!只好用其他方法服务了。」
「很抱歉!面对太太这样的美女,实在很遗憾!」
「是啊,这样有魅力的夫人分开雪白的大腿,我真没有用!下次会努力的,无论如何再给我一次机会。」
尽说一些后悔的话,没有一点色情味,我把耳朵靠在墙上偷听,反而很失望。
不过,父母都不喜欢我偷听,他们说:「要偷听还不如进来看,门是不会上锁的。」
但再怎幺说,我也不想看父母和其他夫妻做交换的现场。
他们不怕这一次的失败,后来有夫妻交换的人来时,还是从早晨就大忙特忙。但这次是不喝酒,决定等到办完事后才喝,所以得能顺利进行。
我知道这种情形,于是我在这次也下了决心。
「我来参观了。」我说完,就在父母的卧室角落下坐着观战,自然全部知道了。
父亲在对方的虽然矮小但身体很丰满、肚子稍微凸出的太太身上,以骑马姿势不停的抽插着。
母亲在对方较瘦的丈夫黑长的东西上坐下,手扶在胸前,屁股一起一落的活动。
当我进去时,父母同时向对方说:「对不起!让她参观吧!妳在那里好好看。」
对方的夫妻剎那间好像很惊讶,但说:「哦!这也是很理想的教育吧!」然后继续进行抽插的工作。
不过,这两对夫妻好像很快就忘记我的存在了。
我的父母参加交换夫妻会,而且对我这个思春的高中三年级的女儿毫不隐瞒,这使我非常的困惑。
有一次,把外国人的夫妻带回来交换夫妻,这个我不管,可是那个外国中年人竟然对我说:「小妞,和我做爱好不好?」
我的同学有人和黑人玩回来后,还十分得意的到处宣扬,但我不喜欢外国人,所以我说:「不!谢谢。」
不过我想,用他来练习外语会话是可以的。
我不理会他的话,自行回到房间去,也懒得参观他们的战事。
又过了不久,父母把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五名男生(据说是G大学夫妻交换研究会的会员)带回来,全体一起和妈妈做爱。
我不愿意看到他们任何人,就一个人躲在房里,可是听到妈妈的大声淫叫,根本没有办法看书。
我平时听到父母的浪声浪语也不会有什幺感觉,但唯有这一次产生奇妙的感觉,于是我就伸手到三角裤里开始手淫。
必须要快一点弄完手淫,使心情平定下来,否则根本不能看书。可是唯有今天几次手淫后都能感到快感,但还是没有办法把心定下来。
我想去厕所,走出房门,看到在厕所前癡呆的站着一名赤裸的学生,腰上围着一条毛巾,垂头沈思着。
我问道: 「你怎幺了?」
不由得二个人的视线相遇,我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感受。
「是……我做不到,我做不到那种事,因为我是要有气氛的人。」
「哦,是吗?可是那样不是吃亏了吗?」
「可是我看到他们受不了,感到难过,我还是须要精神性的。」
他不想留在里面,但又无处可去,只好站在厕所前。
我对他同情了。
「那幺……到我的房间去,怎幺样?」我不由得这样说出来。
「可以那样吗?」
「可以啊!」我彷彿是在引诱这个人。
他乖乖的跟我来到了我的房间,我和他并排地坐在床边,房里除此以外只有书桌和椅子。
此时,从隔壁传来了母亲的叫声:「啊……好……好……还要……还要………」
我心中想着:母亲现在是和第几个人在性交?还有在旁边看的父亲,不知是什幺心情?唉!真不明白大人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幺?我好像能理解,但又不想去理解它。
这时候,我忍不住伸手抱着他的肩,用力的搂紧。这个人的肩很瘦,但很深。
他也伸手到我的腰上,把我拉了过去。
啊……他这时候围在腰上的毛巾前慢慢地凸了起来。我很想伸手去摸,但是我没有这个勇气。
虽然看过很多次父亲赤裸的把这个东西澎涨起来,在母亲的下体进出的样子,但还没有实际摸过男人的这个东西。虽然在很小的时候,洗澡时碰到,但那是软绵绵的状态。
他把我紧紧抱着,把嘴呀在我的嘴上,我不由己的抱紧他,呼吸也急促了起来。
从隔壁又传来母亲的声音:「喔……喔……」好像动物的吼声。
他伸手到我的上衣里面,想脱去我的衣服,但是他实在太笨了,始终脱不下来。我忍不住的自己脱下了上衣,他又想解开我裙子的挂钩,但是还是因为笨拙而解不开,所以还是由我自己站起来,脱掉自己的裙子。
我身上只剩下乳罩和三角裤,就这样他又抱紧了我。
他费了很大的工夫才脱下我的乳罩。
啊!我的乳房露出来了。那是连自己都认为是有弹性的漂亮乳房。
「好美啊!」他讚叹的说道。
「比母亲呢?」我问道。
「嗯,说实话,她的鬆弛的一点,乳头也太黑了。」他说完,就在我的乳房上啾啾地亲吻着。
啊!有一股好强烈的感觉。接吻我是第一次,乳头被吸吮也是第一次。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舒服,现在才知道母亲为什幺喜欢被男人吸吮乳头了。
不过,我还是不喜欢和很多人这样弄,还是和一个人的好。现在,就是这个人的好。
他一面吸吮乳头,一面握住另一个乳房捏弄着。
啊!很舒服!连下面也有一种受到电击的感觉。
「你很会弄,一定有过不少的经验吧?」我问道。
「不!我是第一次,我今天来这里,以为能抛弃童贞,但那种场面太可怕了,所以我还没有性交过。」
哦!这样说来,是童贞和处女在一起啰!他好像很难为情的想掩饰围绕在腰上毛巾的隆起部位。
我假装不经心的样子用手去碰触那个地方,虽然做的很不自然,但这样的举动却使我得到很大的快感。
啊!他的东西很硬,而且有弹性。
我碰到以后,他好像也受到了刺激,他终于按奈不住,开始脱我的三角裤。
我本想抗拒一下,但那样一定会使他放弃行动,所以我就任由他脱掉。
啊!从我的圆圆白白的屁股上取下三角裤了。男人脱我的三角裤,这还是第一次。
在我丰满的雪白大腿间,只长出一点毛,坐在床边看,只能看到小小的三角形。
他也取下围在腰上的毛巾。
啊!那个东西是直立的,孤立的样子很可爱,颜色不像父亲那幺黑。和那些交换夫妻时来的男人比较,他的像笔头花一样孤独可爱。
我很喜欢他的大笔头花,忍不住便伸手紧握着它。
「啊……这样好舒服呀!」他的身体有一点哆嗦。
然后他把我推倒,我搂着他的脖子倒在床上,我怕他看我的那里,因为这是难为情的事,所以抱住他的脖子不放。
「好美,妳的身体真美。」他对我悄悄地说。
当然我和母亲不同,我年轻呀!而且我的腿很长,身材又好,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的。
这时候他把鼻尖靠在我的乳沟上闻着,然后鼻子向下移动,反覆的说:「很香,真的很香。」
其实我没有用香水或任何东西。
我感到刺激很强烈又紧张,知道自己的大腿在颤抖,一方面是难为情,一方面又有很大的期望。
我不由得闭上眼睛,我知道脸已经红到了耳根。
他好像也感受出来,问道:「怕吗?」
「不!不怕!」我说完又紧抱着他。
由于他的身体是抬起的,所以变成我吊在他脖子上的情况。终于他无法支撑我的体重,而被我拉倒,身体落在床上,两人变成上下重叠在一起。
此时,他开始吻我。
啊!真好。
两个人的嘴含在一起,嘴唇紧贴着,同时舌头缠在一块。
他把手伸入我的双腿间,我的身体自然的紧张,想夹紧大腿,可是不知何时他把一条腿放在我的双腿之间,使我没办法夹紧。
啊!他的手指碰到我最敏感的地方,不过他的手好像战战兢兢的样子。
但不灵活的样子也给我更大的好感,很舒服,我的肉缝又溢出了水份。
这时候,又听到母亲在隔壁喊叫的声音:「啊!好……对……对了……就是这里…………」
他终于把手指插入我的肉缝里。
啊!有说不出的妙滋味。
我的身体开始颤抖,我把脸靠在他的胸上,呼吸也急促了。
此刻,我觉得我丰满的身体和他较瘦的身体已经完全贴和了。
他拉我的手去摸他的那根东西。又粗又硬的!不过和父亲交换伙伴的男人比较上也许是小了一点。但太大的好可怕,他这样的最理想,这样的粗度,大概不会很疼痛的进来吧?
我很快的鬆开手,但又下定决心地又将它握在手里。
「真的很硬。」我说。
「第一次吗?」
「嗯,虽然看过,但还是第一次摸到。」
我在他的引导下,慢慢的抚摸着他那坚硬的东西。
头部很光滑,但也像快要爆炸般的勃起,火热的脉动着,大概这是男人感到舒服时的状态吧?
「我什幺也不懂,你教我。」我说道。
「嗯!妳只是这样摸,我就很舒服。」
他又拉我的手到肉茎背面像带状的地方,我在那里开始揉搓。
「啊……舒服……好舒服!」他一面哼一面把手指更深的插入………。
「我可以插进去吗?我想的不得了,本来今天不想这样,因为妳是处女。」
「要……求求你。」我不由得这样说。
我知道有一天须抛弃处女,如果是和他,我愿意…………。
他好像下了决心,拔出手指,再用力拉开我的双腿,身体进入双腿之间,然后看着我的雪白屁股和大腿根部,把坚硬直立的东西顶上来。
我觉得他的硬度已经达到极限。
他用龟头在我湿滑的地方由上向下的磨擦,然后就噗吱一下滑入。
啊!可是不行……只能进去一点点。
「痛啊!」我发出哼声。因为我是处女,大概还有处女膜吧?「不行!进不去。」他好像很伤心。
「痛……痛啊………」我呻吟着。
「那幺……就停止吧?」他体贴的问着我。
「不!我要!」我说着,身体却哆嗦起来。
「我想,大概是短暂的痛吧,请妳忍耐一下。」他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,安慰我。
「我会忍耐的,但是如果太痛,你就要停止动作。」
我双手摀在脸上,分开大腿,等待他的再度开採。
「听说女人要放鬆力量,才不会痛。」他说道。
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放鬆力量?这时候他低下头,在自己的龟头上涂抹口水,然后把我的阴唇分开,将龟头轻轻的插入。
龟头是勉强能进入了,于是他就抱紧我的屁股,慢慢一点一点的插入。此时,我并不感觉疼痛。
突然好像听到噗吱的声音,在这同时他那坚硬的东西一口气地滑了进来。
啊……进来了。
洞里猛然扩张,很舒服,我发出哼声,有一种快窒息的感觉,但却带着一份快感。
我的洞口在他插入的剎那,就开始紧缩,把他的肉棒夹紧,不知道他会不会痛。
「啊……真好!」
他插入后就不动了,好像在欣赏我给他夹紧的滋味。我也在他插入后,身体里抖抖的享受那种感觉。二个人都抖抖的,好像互相做信号,彼此在交谈。
原以为人类是只能用嘴说话,现在知道还能这样沟通。
他搂紧我的屁股,感动之余也不动,静静的享受着合体之美。
「全部进去了吗?」我问道。
「嗯!连根都进去了,现在我们完全密合着。」
「是吗?」我想确定进去的情形,便从屁股下伸手过去摸,摸到的是下面圆圆的附属物。
我吓了一跳,立刻缩手,但在好奇心的驱驶下,我又拿出勇气去摸。他的东西确实从这附属物延伸出去,进入我的腔道里。
我了解后才放开手。但不知为何流出眼泪,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哀,我现在已经不是处女了。
从隔壁又传来母亲的声音,但这次很快就听不见了。
这时候他开始慢慢的活动起来。
啊!真甜美啊!已经完全不痛了,却有着莫大的快感。
好像多年来听到隔壁父母的恼人声音累积的烦闷,总算发洩出来了。
他开始用力进出,感觉出我内部的肉缠在他的东西上,随着活动和磨擦。
那真是一种快感…………。
「啊!真好,原来是这样好,女人的这里没有想到会这样好。」他兴奋地说着。
而此时,我也快要溶化了。
「这样好不好?好吗?这样呢?」
他做着各式各样的动作,但什幺样都好,我实在分不出来。
肉洞里固然好,但他的毛在我最敏感的地方磨擦也非常好。
「我这一生,不想和别人干这件事了。」
「我也是,我们结婚好不好?」他问道。
「嗯……可以!」
不过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,住处也不知道。
啊……不过能永远做这种舒服的事,而且能和父母一样享受性交的乐趣,我恨不得马上就结婚。
「啊!好啊!啊啊…………」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妙的感受,大声叫了出来,全身都颤抖着,同时快感向全身的每一个毛细孔扩散。
紧张和鬆弛交换来临了…………。
「啊……我……不行了……….」
G大学的学生突然激烈活动起来,强而有力的冲刺着,然后全身一阵哆嗦。
啊……他是在射精了。
也许我会怀孕,可是没有关係,我会和他结婚。
我这样想着,禁不住地紧抱着他,从下面向上挺起屁股,然后两个人紧紧缠在一起…………。
从此以后,我就迷恋上性交。
没有什幺事能这样舒服,心里有美的罗曼蒂克,产生积极生活的意念,事后又感到爽快的事。
可是别人家里,当女孩的乳房隆起或有月经时,不是父亲不要,就是女儿不肯在一起洗澡了。
我是怕朋友问到时会难为情,就不再和父亲一起洗澡。可是,我的父母在洗完澡时,光着身体在家里走来走去,他们都不在意自己的举动,反而我感到难为情。
我有时看不惯,就说:「别人家都不是这样,把浴巾围在身上吧!」
「本来就有的东西为什幺要掩饰,说起来妳还是从我这里生出来的。」父亲说完后,还故意摇动垂在胯下的东西给我看。
不说父亲吧,母亲也裸露丰满的乳房或屁股到处走动。
我说:「不要这样!有同学来的话,那多难为情。」
「妳胡说什幺,妳可是吃这个奶长大的。不过我的形状没有变,和年轻时一样。」母亲说着,用手托起乳房站在镜子前陶醉一番。
甚至有一次洗澡时,母亲用手指拨开她的那里要我看,还说:「妳来看,妳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。」
我害羞的逃走,但母亲还追到我的房间,问我到底是怎幺回事。
还有,我本来早就会手淫了,不过是在桌角上摩擦的幼稚行为。
有一次偶然的被母亲看到,可是她却说:「妳这是干什幺,不要这样,要把手指洗乾净消毒好,用手指弄才舒服,用桌角可能使那重要的地方受伤,妈妈做给妳看吧!」
「不要!不要!」我在感到难为情以前,先产生无奈感。
但也许是为性行为不产生罪恶感,父母独特的性教育吧。因为是这样长大的,我对手淫被发觉的事,并没有对父母感到难为情,或像朋友那样因此怨恨父母。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家的父母比别人家是过份了。
因为母亲在性交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,而且父亲也好像喜欢性交,不是每天也至少二天有一次。
当我睡眼迷糊有事去父母亲的卧室时,父母会毫不隐藏的,由母亲赤裸的骑在父亲的身上,拼命的扭动雪白的屁股。
我从小就看过很多次父母性交的场面,当初还以为是在摔跤,但慢慢的也觉得不对。
「你们做什幺?不是摔跤吗?」我这样问着。
「不是摔跤,现在我们在做非常舒服的事。孩子,妳长大以后也要找个好男人多多干这种事的。啊……好……好……好的不得了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…」母亲一面说一面骑在父亲的身上猛烈扭动着屁股。
我蹲在母亲的身边,看父亲的东西在母亲的身体里进进出出的模样,但是并没有感到色情,只想到大人会做奇妙的事。
所以我去幼稚园时,就对隔壁的男同学说:「我们来玩爸爸妈妈的游戏。」
「哦!办家家酒啊?有饭碗什幺吗?」他说。
「不是的!你要脱下裤子睡在这里,我在上面,是这样的。」我说着,就让他仰卧在塑胶布上,再把他的小鸡鸡拉出来。
当我想骑上去时,老师发现就立刻跑出来,并喊着:「你们在干什幺?」
我一脸茫然的回答:「我们在做爸爸妈妈的事。」
这件事还是成了问题,父母被老师叫去训戒一番,母亲好像也很困扰的样子,可是母亲对我说:「不可以在幼稚园做那种事,不要对别人做,只有在家里才可以。」
听说在挪威或瑞典等国家就有类似这种教育,我还弄不清那一种比较好。
后来我为升学考试,开始用功读书时,每天晚上母亲的声音太吵了,我有时会忍不住去敲他们的房门,提出抗议:「小声一点好不好!」
母亲总是用陶陶然的声音说:「对不起!但是太舒服了……….」
不知道她的精神是不是有问题。我想,这样的父母已经难以救药,但也不会恨他们的。
可是父母性交时的声音,我并不觉得淫蕩。但我对性交没有多大兴趣,也很少手淫了。
也许是这样的关係,所以没有男朋友。虽然常接到情书,但不想一对一的交往。
有时,母亲还会很多心的说:「妳这年龄想性交也是应该,但一定要用保险套,这个桌子里有保险套,妳会用吗?不然就给爸爸套上练习。」
母亲的玩笑是不是太过份了。
不过,当父母认真的开始所谓『夫妻交换』的游戏时,我确实吓了一跳。
我提出抗议,可是母亲说:「爸妈和小孩有不同的生活,小孩有小孩的生活,把妳好好养大成人是我们的义务,但不会限制妳的自由,所以妳也不能限制爸妈的自由。」
这样我有什幺办法呢?而且又觉得父母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
和别人的父母只準自己做好事,孩子交异性朋友就生气或限制自由,或只因自己是大人就对孩子施威,或仅因养育就对孩子施加压力,根本不理会孩子只顾看电视的父母完全不同。
说起来我家就没有电视,晚餐都是一家三口在一起愉快的吃。父母的主张是吃饭看电视会削减亲子关係。据说别家的父亲阻止孩子想看的节目,而看自己要看的相扑或棒球。这一点我是感谢父母,不过现在仔细回想,父母是只对色情有兴趣,对其他的节目根本不关心。
不过,父亲大概和别人不一样,父亲从来没有骂过孩子。他说:「人类就是为做自己爱做的事出生,家庭也是各自为政的人集合在一起,能让家人做多少自己喜欢做的事,就看父亲的度量。」
回想起来,我确实没有挨骂过,有没有受到干涉。
高二时,向父母商量报考什幺学校或就业时,父母说:「妳已经是高中生,自己决定吧!和我们商量,我们得负责任。」
不知是有理解还是不负责任。
这些暂且不说,父母最近好像对交换夫妻发生极大兴趣。父母对我说:「我们要做交换夫妻了,大概交换对方的夫妻或有其他男女会来家里,但妳不要太在意。」
而且母亲笑嘻嘻的,好像很高兴的说:「妈妈在那时候的声音会很大,但妳已习惯了,不会在乎吧?」
实在是太开放了,我不知该说些什幺才好。
不知是父亲先提出,还是母亲建议的,总之把夫妻的照片送去夫妻交换杂誌刊登。因为也没有掩饰面孔,立刻被公司的同事们知道,马上成为相当大的问题,可是父亲一点也不在乎的说:「又没有妨碍到别人,有那里不对?而且看这种照片的人也是对夫妻交换有兴趣吧,和我们来一次如何?还可以在公司里扩大夫妻交换的领域。」
大家似乎都哑口无言,也就不了了之。
事后,父亲还对上司说:「要不要到我家和我内人性交,她是不错的名器呢!」
对公司的女职员也说:「到我家来和我们一起玩吧!我对性交是有信心的。」
大家都拿他没有办法,但大家也没有对他产生恶感。
这一些暂且不说,现在报告交换夫妻的对方第一次来我家的情形。
父母都从早晨(星期天)就开始紧张的忙碌着,做寿司、準备酒、打扫房间、换新洗的床单等欢迎的準备。
黄昏时刻来的夫妻,是给人好感的教员夫妻。因为我的父母很大方的劝酒吃菜,好像非常感动,结果两个男人都大醉,什幺也做不成了。
我在自己的房里隔墙听的一清二楚。
「妳那边不行吗?这边也不行。」
「男人真没有用,太太吸吮我丈夫的东西吧,也许这样是有用的。」
「是啊!我在努力的吸吮呀!」
「你真没有用!好吧,我也努力吸吮。」
「对不起!太抱歉!只好用其他方法服务了。」
「很抱歉!面对太太这样的美女,实在很遗憾!」
「是啊,这样有魅力的夫人分开雪白的大腿,我真没有用!下次会努力的,无论如何再给我一次机会。」
尽说一些后悔的话,没有一点色情味,我把耳朵靠在墙上偷听,反而很失望。
不过,父母都不喜欢我偷听,他们说:「要偷听还不如进来看,门是不会上锁的。」
但再怎幺说,我也不想看父母和其他夫妻做交换的现场。
他们不怕这一次的失败,后来有夫妻交换的人来时,还是从早晨就大忙特忙。但这次是不喝酒,决定等到办完事后才喝,所以得能顺利进行。
我知道这种情形,于是我在这次也下了决心。
「我来参观了。」我说完,就在父母的卧室角落下坐着观战,自然全部知道了。
父亲在对方的虽然矮小但身体很丰满、肚子稍微凸出的太太身上,以骑马姿势不停的抽插着。
母亲在对方较瘦的丈夫黑长的东西上坐下,手扶在胸前,屁股一起一落的活动。
当我进去时,父母同时向对方说:「对不起!让她参观吧!妳在那里好好看。」
对方的夫妻剎那间好像很惊讶,但说:「哦!这也是很理想的教育吧!」然后继续进行抽插的工作。
不过,这两对夫妻好像很快就忘记我的存在了。
我的父母参加交换夫妻会,而且对我这个思春的高中三年级的女儿毫不隐瞒,这使我非常的困惑。
有一次,把外国人的夫妻带回来交换夫妻,这个我不管,可是那个外国中年人竟然对我说:「小妞,和我做爱好不好?」
我的同学有人和黑人玩回来后,还十分得意的到处宣扬,但我不喜欢外国人,所以我说:「不!谢谢。」
不过我想,用他来练习外语会话是可以的。
我不理会他的话,自行回到房间去,也懒得参观他们的战事。
又过了不久,父母把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五名男生(据说是G大学夫妻交换研究会的会员)带回来,全体一起和妈妈做爱。
我不愿意看到他们任何人,就一个人躲在房里,可是听到妈妈的大声淫叫,根本没有办法看书。
我平时听到父母的浪声浪语也不会有什幺感觉,但唯有这一次产生奇妙的感觉,于是我就伸手到三角裤里开始手淫。
必须要快一点弄完手淫,使心情平定下来,否则根本不能看书。可是唯有今天几次手淫后都能感到快感,但还是没有办法把心定下来。
我想去厕所,走出房门,看到在厕所前癡呆的站着一名赤裸的学生,腰上围着一条毛巾,垂头沈思着。
我问道: 「你怎幺了?」
不由得二个人的视线相遇,我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感受。
「是……我做不到,我做不到那种事,因为我是要有气氛的人。」
「哦,是吗?可是那样不是吃亏了吗?」
「可是我看到他们受不了,感到难过,我还是须要精神性的。」
他不想留在里面,但又无处可去,只好站在厕所前。
我对他同情了。
「那幺……到我的房间去,怎幺样?」我不由得这样说出来。
「可以那样吗?」
「可以啊!」我彷彿是在引诱这个人。
他乖乖的跟我来到了我的房间,我和他并排地坐在床边,房里除此以外只有书桌和椅子。
此时,从隔壁传来了母亲的叫声:「啊……好……好……还要……还要………」
我心中想着:母亲现在是和第几个人在性交?还有在旁边看的父亲,不知是什幺心情?唉!真不明白大人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幺?我好像能理解,但又不想去理解它。
这时候,我忍不住伸手抱着他的肩,用力的搂紧。这个人的肩很瘦,但很深。
他也伸手到我的腰上,把我拉了过去。
啊……他这时候围在腰上的毛巾前慢慢地凸了起来。我很想伸手去摸,但是我没有这个勇气。
虽然看过很多次父亲赤裸的把这个东西澎涨起来,在母亲的下体进出的样子,但还没有实际摸过男人的这个东西。虽然在很小的时候,洗澡时碰到,但那是软绵绵的状态。
他把我紧紧抱着,把嘴呀在我的嘴上,我不由己的抱紧他,呼吸也急促了起来。
从隔壁又传来母亲的声音:「喔……喔……」好像动物的吼声。
他伸手到我的上衣里面,想脱去我的衣服,但是他实在太笨了,始终脱不下来。我忍不住的自己脱下了上衣,他又想解开我裙子的挂钩,但是还是因为笨拙而解不开,所以还是由我自己站起来,脱掉自己的裙子。
我身上只剩下乳罩和三角裤,就这样他又抱紧了我。
他费了很大的工夫才脱下我的乳罩。
啊!我的乳房露出来了。那是连自己都认为是有弹性的漂亮乳房。
「好美啊!」他讚叹的说道。
「比母亲呢?」我问道。
「嗯,说实话,她的鬆弛的一点,乳头也太黑了。」他说完,就在我的乳房上啾啾地亲吻着。
啊!有一股好强烈的感觉。接吻我是第一次,乳头被吸吮也是第一次。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舒服,现在才知道母亲为什幺喜欢被男人吸吮乳头了。
不过,我还是不喜欢和很多人这样弄,还是和一个人的好。现在,就是这个人的好。
他一面吸吮乳头,一面握住另一个乳房捏弄着。
啊!很舒服!连下面也有一种受到电击的感觉。
「你很会弄,一定有过不少的经验吧?」我问道。
「不!我是第一次,我今天来这里,以为能抛弃童贞,但那种场面太可怕了,所以我还没有性交过。」
哦!这样说来,是童贞和处女在一起啰!他好像很难为情的想掩饰围绕在腰上毛巾的隆起部位。
我假装不经心的样子用手去碰触那个地方,虽然做的很不自然,但这样的举动却使我得到很大的快感。
啊!他的东西很硬,而且有弹性。
我碰到以后,他好像也受到了刺激,他终于按奈不住,开始脱我的三角裤。
我本想抗拒一下,但那样一定会使他放弃行动,所以我就任由他脱掉。
啊!从我的圆圆白白的屁股上取下三角裤了。男人脱我的三角裤,这还是第一次。
在我丰满的雪白大腿间,只长出一点毛,坐在床边看,只能看到小小的三角形。
他也取下围在腰上的毛巾。
啊!那个东西是直立的,孤立的样子很可爱,颜色不像父亲那幺黑。和那些交换夫妻时来的男人比较,他的像笔头花一样孤独可爱。
我很喜欢他的大笔头花,忍不住便伸手紧握着它。
「啊……这样好舒服呀!」他的身体有一点哆嗦。
然后他把我推倒,我搂着他的脖子倒在床上,我怕他看我的那里,因为这是难为情的事,所以抱住他的脖子不放。
「好美,妳的身体真美。」他对我悄悄地说。
当然我和母亲不同,我年轻呀!而且我的腿很长,身材又好,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的。
这时候他把鼻尖靠在我的乳沟上闻着,然后鼻子向下移动,反覆的说:「很香,真的很香。」
其实我没有用香水或任何东西。
我感到刺激很强烈又紧张,知道自己的大腿在颤抖,一方面是难为情,一方面又有很大的期望。
我不由得闭上眼睛,我知道脸已经红到了耳根。
他好像也感受出来,问道:「怕吗?」
「不!不怕!」我说完又紧抱着他。
由于他的身体是抬起的,所以变成我吊在他脖子上的情况。终于他无法支撑我的体重,而被我拉倒,身体落在床上,两人变成上下重叠在一起。
此时,他开始吻我。
啊!真好。
两个人的嘴含在一起,嘴唇紧贴着,同时舌头缠在一块。
他把手伸入我的双腿间,我的身体自然的紧张,想夹紧大腿,可是不知何时他把一条腿放在我的双腿之间,使我没办法夹紧。
啊!他的手指碰到我最敏感的地方,不过他的手好像战战兢兢的样子。
但不灵活的样子也给我更大的好感,很舒服,我的肉缝又溢出了水份。
这时候,又听到母亲在隔壁喊叫的声音:「啊!好……对……对了……就是这里…………」
他终于把手指插入我的肉缝里。
啊!有说不出的妙滋味。
我的身体开始颤抖,我把脸靠在他的胸上,呼吸也急促了。
此刻,我觉得我丰满的身体和他较瘦的身体已经完全贴和了。
他拉我的手去摸他的那根东西。又粗又硬的!不过和父亲交换伙伴的男人比较上也许是小了一点。但太大的好可怕,他这样的最理想,这样的粗度,大概不会很疼痛的进来吧?
我很快的鬆开手,但又下定决心地又将它握在手里。
「真的很硬。」我说。
「第一次吗?」
「嗯,虽然看过,但还是第一次摸到。」
我在他的引导下,慢慢的抚摸着他那坚硬的东西。
头部很光滑,但也像快要爆炸般的勃起,火热的脉动着,大概这是男人感到舒服时的状态吧?
「我什幺也不懂,你教我。」我说道。
「嗯!妳只是这样摸,我就很舒服。」
他又拉我的手到肉茎背面像带状的地方,我在那里开始揉搓。
「啊……舒服……好舒服!」他一面哼一面把手指更深的插入………。
「我可以插进去吗?我想的不得了,本来今天不想这样,因为妳是处女。」
「要……求求你。」我不由得这样说。
我知道有一天须抛弃处女,如果是和他,我愿意…………。
他好像下了决心,拔出手指,再用力拉开我的双腿,身体进入双腿之间,然后看着我的雪白屁股和大腿根部,把坚硬直立的东西顶上来。
我觉得他的硬度已经达到极限。
他用龟头在我湿滑的地方由上向下的磨擦,然后就噗吱一下滑入。
啊!可是不行……只能进去一点点。
「痛啊!」我发出哼声。因为我是处女,大概还有处女膜吧?「不行!进不去。」他好像很伤心。
「痛……痛啊………」我呻吟着。
「那幺……就停止吧?」他体贴的问着我。
「不!我要!」我说着,身体却哆嗦起来。
「我想,大概是短暂的痛吧,请妳忍耐一下。」他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,安慰我。
「我会忍耐的,但是如果太痛,你就要停止动作。」
我双手摀在脸上,分开大腿,等待他的再度开採。
「听说女人要放鬆力量,才不会痛。」他说道。
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放鬆力量?这时候他低下头,在自己的龟头上涂抹口水,然后把我的阴唇分开,将龟头轻轻的插入。
龟头是勉强能进入了,于是他就抱紧我的屁股,慢慢一点一点的插入。此时,我并不感觉疼痛。
突然好像听到噗吱的声音,在这同时他那坚硬的东西一口气地滑了进来。
啊……进来了。
洞里猛然扩张,很舒服,我发出哼声,有一种快窒息的感觉,但却带着一份快感。
我的洞口在他插入的剎那,就开始紧缩,把他的肉棒夹紧,不知道他会不会痛。
「啊……真好!」
他插入后就不动了,好像在欣赏我给他夹紧的滋味。我也在他插入后,身体里抖抖的享受那种感觉。二个人都抖抖的,好像互相做信号,彼此在交谈。
原以为人类是只能用嘴说话,现在知道还能这样沟通。
他搂紧我的屁股,感动之余也不动,静静的享受着合体之美。
「全部进去了吗?」我问道。
「嗯!连根都进去了,现在我们完全密合着。」
「是吗?」我想确定进去的情形,便从屁股下伸手过去摸,摸到的是下面圆圆的附属物。
我吓了一跳,立刻缩手,但在好奇心的驱驶下,我又拿出勇气去摸。他的东西确实从这附属物延伸出去,进入我的腔道里。
我了解后才放开手。但不知为何流出眼泪,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哀,我现在已经不是处女了。
从隔壁又传来母亲的声音,但这次很快就听不见了。
这时候他开始慢慢的活动起来。
啊!真甜美啊!已经完全不痛了,却有着莫大的快感。
好像多年来听到隔壁父母的恼人声音累积的烦闷,总算发洩出来了。
他开始用力进出,感觉出我内部的肉缠在他的东西上,随着活动和磨擦。
那真是一种快感…………。
「啊!真好,原来是这样好,女人的这里没有想到会这样好。」他兴奋地说着。
而此时,我也快要溶化了。
「这样好不好?好吗?这样呢?」
他做着各式各样的动作,但什幺样都好,我实在分不出来。
肉洞里固然好,但他的毛在我最敏感的地方磨擦也非常好。
「我这一生,不想和别人干这件事了。」
「我也是,我们结婚好不好?」他问道。
「嗯……可以!」
不过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,住处也不知道。
啊……不过能永远做这种舒服的事,而且能和父母一样享受性交的乐趣,我恨不得马上就结婚。
「啊!好啊!啊啊…………」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妙的感受,大声叫了出来,全身都颤抖着,同时快感向全身的每一个毛细孔扩散。
紧张和鬆弛交换来临了…………。
「啊……我……不行了……….」
G大学的学生突然激烈活动起来,强而有力的冲刺着,然后全身一阵哆嗦。
啊……他是在射精了。
也许我会怀孕,可是没有关係,我会和他结婚。
我这样想着,禁不住地紧抱着他,从下面向上挺起屁股,然后两个人紧紧缠在一起…………。
从此以后,我就迷恋上性交。
没有什幺事能这样舒服,心里有美的罗曼蒂克,产生积极生活的意念,事后又感到爽快的事。